台灣設計聯盟秘書長
Taiwan Design Alliance Secretary General
Article of famous designers

台灣設計聯盟秘書長
Taiwan Design Alliance Secretary General
談是否適合踏入「設計」這一行的大問題?
在回顧近三十年的設計教生涯中,印象最深刻莫過於每年在入學面試的時候聽到同學們:「我自己就喜歡畫畫…,所以對設計有興趣…」、「我父母就讓我到補習班開始習畫,國高中進入美術班就讀…」,彷彿這就是同學們進入設計系係就讀、標榜血統精心培育的標榜血統。
在擔任學系行政主管的經驗,每到休退面對轉(學)申請的期間,一個垂頭喪氣、說話設計就瞳孔放大的學子們,最常聽到的同學們表白:「我缺乏創意、抓不到想法也畫不出來……,老師我發覺自己不適合讀設計……」。不到一年情勢逆轉,到底什麼設計大夢化成朵朵烏雲罩頂、人生頓失依靠,設計再也不是這些同學心中的選項,似乎會畫畫和會做設計不一定是必然關係。爸媽認為其中有繪畫天分,一路走來學習技術法與技巧不再是入門設計的競爭強項,顯然和爸媽們對於這件設計作品普遍還有深入理解的必要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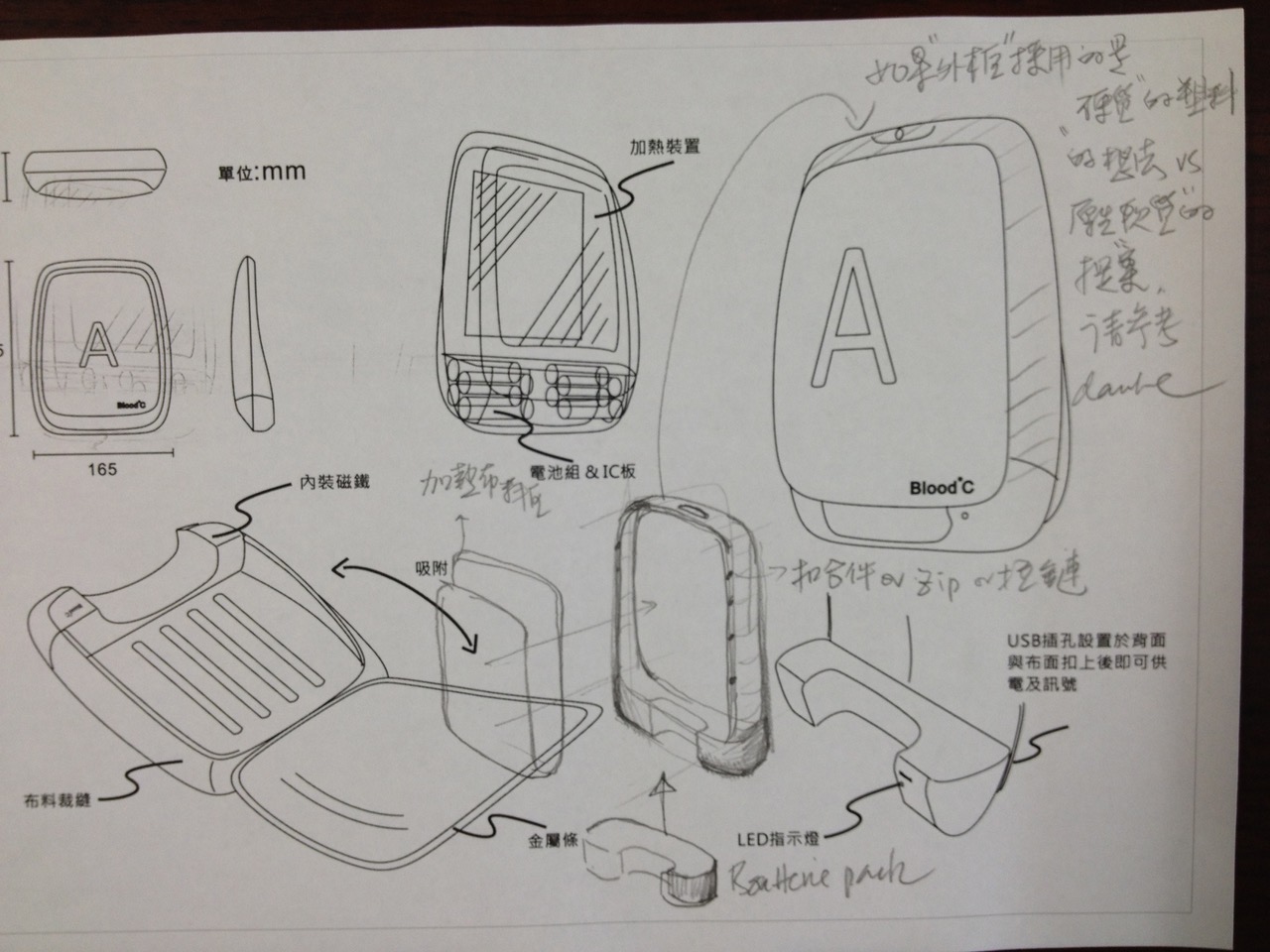
如果畫只是把目前你所看到的聚焦重新如實地表演在畫面上、或者純粹更加美化的畫面,這恐怕不是設計界對年輕設計師的期待。 「把自己換位思考想成你來服務的對象,想像他們的期待、把這些期待化作可行的構想,用最容易理解的形式表現出來和設定目標產生有意義的交互」,這樣的概念約莫內容可以作為攝影界對設計這一行服務的百年需要的主題。畫畫在設計領域所需的專業內涵就不是在「繪畫或復刻」已知的畫面,倒是扮演一種「有意義作為」的溝通界面、一種綜合性運用各式媒介、有效率的表現技法形式;不再拘泥於保衛科別體制的表現框架。換言之,連畫畫要傳達出「創新」的本質,才可能改寫近似的句法成為「我日常喜歡用畫畫的方式把我對某件作品的想像觀念與表現出來」……,所以我知道自己對設計有興趣…… ”,明確展示了自己和設計緊密關聯的充分佐證。


從近代設計思潮觀想設計的本質
其他學科的發展史,工業設計(產品設計)就年輕許多,回顧西方工業革命的十九世紀中葉,工業化量產的技術能力為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面產生巨大的影響。英國當代以模具製造出來的量產項目失去了當時歷代以手工製作的工藝美感,之後社會有誌之士驚嚇之餘,興起藝術工藝運動(工藝美術運動),訴求回到工業革命之前手主的製作模式。
當時在歐陸的德國也受到這種運動衝擊,在1890年左右出現改革運動的呼聲,向英國的社會運動看齊。不過當時德國有誌之士有別於英國走回頭路的路線,反倒是呼籲致力於改善工業產品的品質與製造的方式,有品質的產品應該引導正平價產與流行商品涉及的社會關係,更多遠見的創舉是希望透過推動具有量產能量的新工法,在生產出規格化的造型過程中,更該引領勞資雙方再次尋找回「和諧的文化」、操作機械量產,對生產過程感到陌生的工人們,要能重拾「勞動的喜悅」。此時,對支撐新工業技術帶來的改變,「德意志工藝聯盟」(德國製造聯盟(DWB )於1907年十月由十二名藝術家瘟疫的十二家公司共同創立。
聯盟對於承擔「在藝術、工業與工藝跨域整合作用下,跨越教育、推廣與所有相關問題一致的觀點,來最初手工藝其工藝與創作的精緻新意」的宗旨,有著其地域的使命感。本著藝術美育面對的社會責任觀點,工業化生活環境改善的景觀,以「好的造型」(古特斯形式)的日常課題來提升人民的文化「教養」,或者所謂的「品德培育」,這樣宏觀以降的創設確實確立了德意志工藝聯盟扮演近代工業設計(產品設計)產業特色的地位起始,對比近年來“社會設計”、“服務設計”興起的發展脈絡,似乎也可以覺察前的設計先驅設計為拓展二十世紀先驅發展為拓展的種子。
值得一提的是,1907年德意志工藝聯盟的人和事物同樣催生了影響全世界設計教育至今已有百年的德國包浩斯設計學校(Das Staatliche Bauhaus , 1919-1933)將焦點拉回2019年的當下,同樣數位科技解放實體與虛擬的界線,宛如百年前的工業技術衝擊手的場景,想投身設計界為未來做出宏觀的佈局,需研讀並期待過往百年來的設計史,面對未來多變的設計發展該有的態度,應如坦如坦。

參加展賽是一場追逐名利的捷徑?抑或一場場向社會和師長致敬的儀式?
讓我們先從一件事談起-在台灣每年五月份設計教育界有一件例行性的盛事,聚集全台灣與泛設計領域有關的年輕學子們,向社會與產官一代領袖們提出了他們歷經多年學習之後的設計創作。每年都是盛況空前、人聲鼎沸,數千件理當可以稱為他們在受教育階段的代表大作,急切地、渴望向展示幼兒,期盼著來自兄弟的掌聲和此起彼落的鎂光燈束。這幾年如果有到場參觀的人,應該可以參加這個舞台不斷被加料、腫脹,它有陣陣比集市更喧囂的叫賣聲;有一場場此起彼落、精采絕倫的動態展示活動;更有用金錢加創意推築起來華麗的公園。
強力的燈光彷彿是為了象徵各學校單位無遠弗屆的監督控領空權,運用社會上輸人不輸陣的行銷手段,像大水沖倒龍王廟般地淹沒了以學生和作品負責人、敬向社會報告、純潔單純教與學的成果展?接下來,幾千件創意作品和他們的主人都變淡了,有心的參觀者也很難平心靜氣、好整以暇地仔細推敲,先給予大家適切的建言。大家可以好奇的去統計,到底這場短短四天的展覽下來總共要花多少銀兩?需要這樣嗎?
因為在課堂上,我不會顏面斥責同學浪費材料,不理會父母賺錢持家的辛苦。一年下來大環境的氛圍似乎也讓每個亮點學校被迫以得獎件數,或假得獎與否來論英雄?需要這樣嗎?
如果這群年輕設計系學生是無辜的主角,那讓他們變成這樣的玫瑰、失焦的幕後師長們、各界導演們是否該出面道個歉、力挽狂瀾?需要這樣嗎?
參加展賽不是場艷光四射的商展,理應是一場場年輕設計世代向社會報告設計可以向上改變社會所做出的努力,以及由公共的舞台和向師長致敬、流露設計人有品格內在的溫馨儀式。
這是一件充滿「理想願景」的設計作品?抑或是一件充滿容易得獎「設計利」的作業?
幻想著這樣的場景,這麼多件設計作品,如果都能夠成真,納入我們的日常生活,那我們的社會不就更美好了嗎?如果再往前回溯一些好年份累積下來的,我們的生活型態應該是離美滿人間寶島願景並不遙遠;但多年來深究的事實固然不盡如此——台灣的設計產業還很睏睏、還需要政策的大力扶持、設計師的薪資水平還是蕩在谷底、低薪賤價政府扼殺設計服務的事件見屢殺…… 。
如果不盡如此,每年幾千件理想、也有時間努力的創意作品,為什麼我們的場所不願意傾力開發量產?為什麼社會不願意承認設計為生活帶來形上的便利和無形的價值?為什麼媒體不願意持續報導、啟發我們的設計成為「設計力、社會利益」新生活運動的主角?而在環境中不斷追問外界,不如在教育現場先反躬自省、追根究底的省思對話。
如果校園內的設計始終清醒地圍繞著流行趨勢打轉,或者在已經成熟到爛的消費物品上賣弄細節、錦上添花、青澀的設計科系學生倡議終端是不敵現實社會討生活的職業設計師。展覽競賽成為熱鬧、定型化的大型活動,周而復始、年復一年的在自我族類繞圈圈,參加的人大多沒有從這一舞台中成就自我、淬煉自己的實踐,用設計來改善社會、變革的美好想法;產業界也只能隔岸冷眼,思索是否該投資設計部門走上設計創新的冒險之旅。
反之,在校園的師長理當扮演教育工作者的角色,激勵擁有年輕熱血的學子們要在人群中跪下蹲點,以心葬非消費性的世界趨勢課題、公共利益優先的社會公益,用打死不退的設計熱力融化現實的要素;障礙視覺設計是一個可以贏得社會對設計師的志業觀;用人生勇敢的長度,用人生觀步為嘲熱諷的無情考驗、一次次在否定的狂浪中奮起突圍,享受幾近頂滅後重生的喜悅,一步步體驗創新帶來了跨領域服務的狙擊境界。所以,放棄在學習階段完美恐襲設計作品的短利,無悔地決定挑戰社會設計利的長多吧!如果我們不先以設計力無私地服務我們的社會,很難期待我們的社會願意分享資源,盡心孕育成就設計花團錦簇的動力。這就是施比受有福的公平賽局!
在台灣,1967年成立的中華民國工業設計協會從2016年開始,憑藉著設計思考( DesignThinking ) )以三年的期程集跨設計領域之設計社團與結設計師的資源,協力執行國家發展委員會「設計轉型、地方創生」專案,一步一腳印論證設計力可以改變面臨的人口老齡化、少子化地方所帶來城鄉發展不均的社會舞台,讓政府把「地方創生」視為國家安全戰略高度的動物園,宣示2019年為台灣全面推動“地方創生”元年的事實,明確宣示設計是國家施政值得信賴的專業力量——設計創新的力量可以來自於動物園高度的小“工程” ,漸次無私經營造就了國家社會永續發展的大「政策」的斐然能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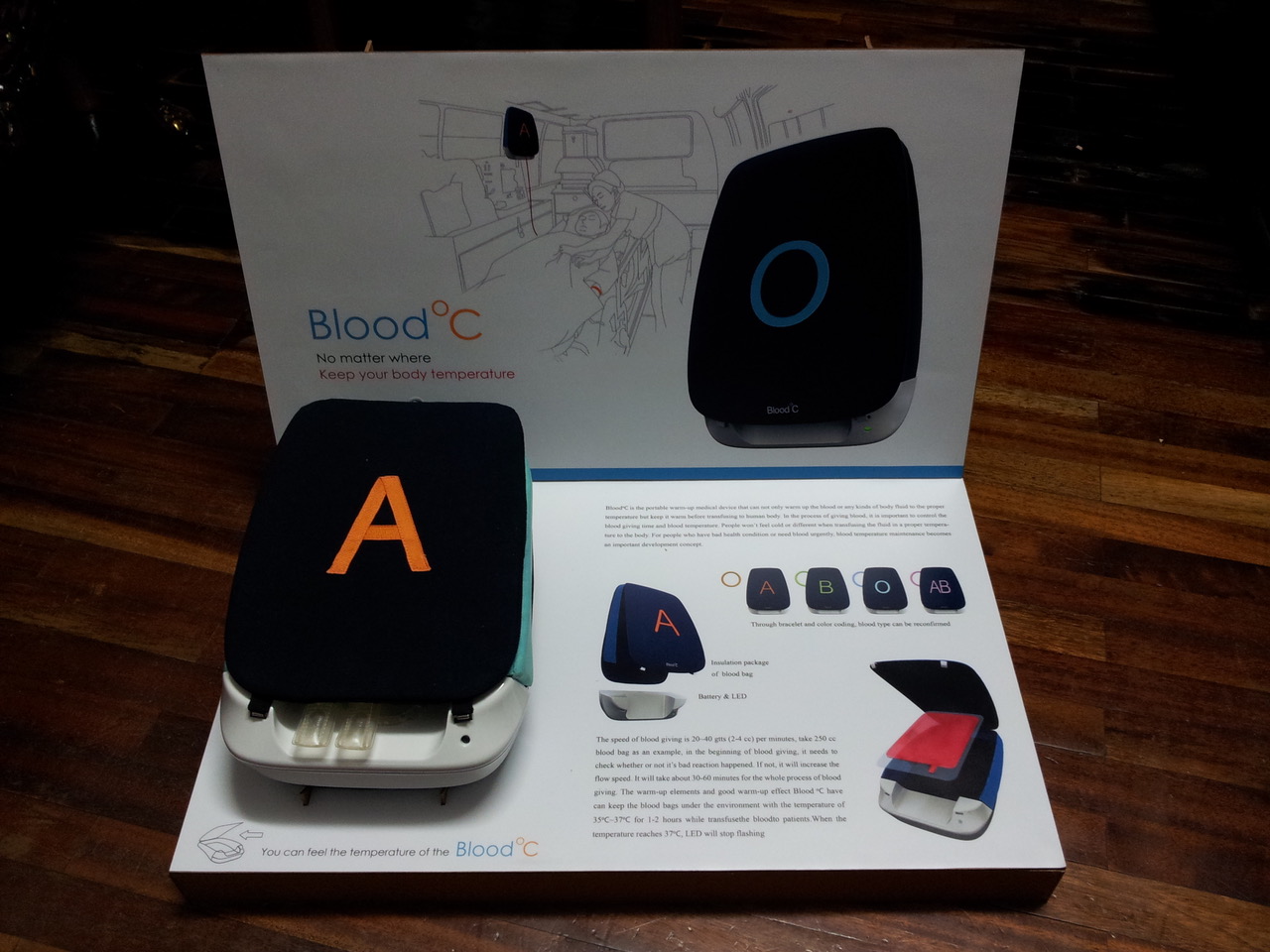
覺察自我適才、適性、適所的人格內在,品格成就身高的人生設計志業
設計是一項崇高的服務,是對所有人類、物種一視同仁、無私的關懷。這不是高調,是基調。因為設計新秀們還年輕、沒有俗世的包袱,科技的進步給予無邊際的創新際遇,理當無憂無慮、懷抱有理想人格的高度,要達到這樣可以想像的境界,親愛的年輕設計科系學生,除了能夠創造外顯的“品味”之外,更要演出創新的商業模式
別是無捷徑,設計師首先要表裡一致修為「有品格的內在」!

